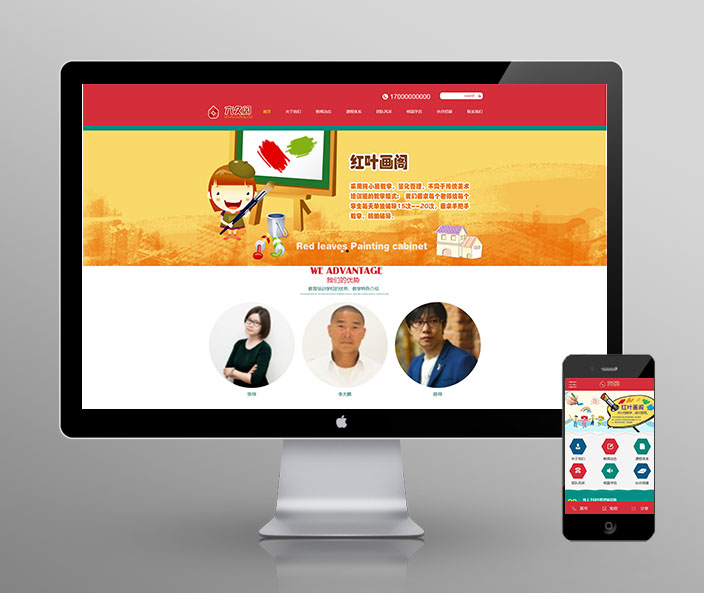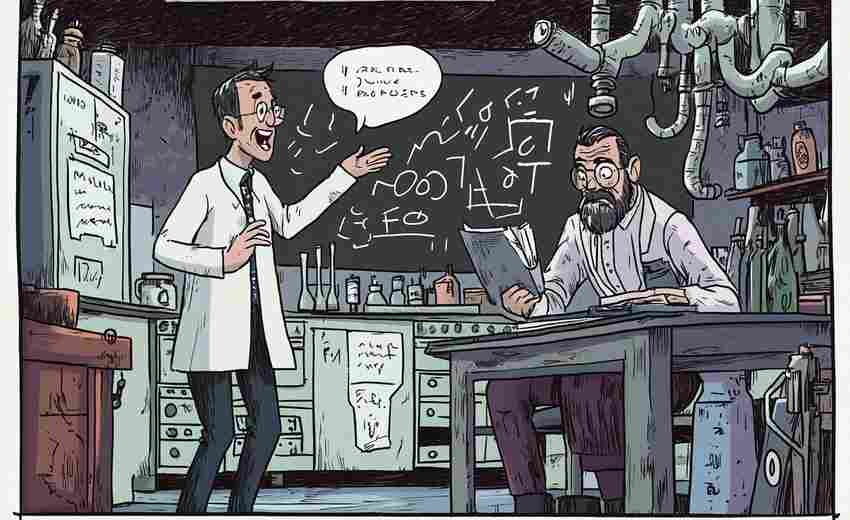随着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,个人数据已成为社会运转的“新石油”,但数据滥用与隐私泄露的隐患也随之显现。全球范围内,从欧盟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(GDPR)到中国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,法律框架逐渐构建起个人数据权利的防护网。这些法律不仅赋予个体对自身数据的控制权,还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,在数据流通与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。在这一进程中,如何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切实的个体权利保障,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。
确权基础与法律依据
数据权益的确权是法律保护的起点。《民法典》第127条首次将数据纳入民事权益范畴,其开放性条款设计为后续立法提供了接口。王利明指出,数据权益具有复合性特征,既包含人格属性(如隐私权、个人信息权),又涉及财产价值(如企业数据资产),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传统物权或知识产权制度无法完全覆盖。司法实践中,北京互联网法院在“李永卓与抖音案”中,明确用户浏览记录属于关联性个人信息,行使查阅权需平衡多方主体权益,这体现了数据确权在司法维度的具体化。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13条构建了“知情同意为核心,六种法定情形为补充”的合法性基础体系。在“许某诉京东案”中,法院认定用户使用平台即构成对促销短信的默示同意,但强调处理者必须提供便捷的退出机制。这种司法认定既维护了数据处理效率,又坚守了用户自主决定权边界。值得注意的是,GDPR创设的“数据携带权”虽未在我国法律中直接规定,但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45条关于个人信息转移的规定,已为类似权利的本土化预留空间。
知情同意机制的实质化
传统“全有或全无”的同意模式在数字经济中面临挑战。社交媒体平台常以打包授权方式获取超范围数据权限,用户往往在未充分理解条款的情况下被动同意。对此,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14条要求同意必须“自愿、明确”,广州互联网法院在“麦海波案”中,认定未经律师本人同意公开执业信息构成侵权,凸显了形式同意与实质同意的司法审查差异。
动态同意机制的探索成为破局关键。欧盟GDPR要求数据处理目的变更需重新获取同意,我国司法实践亦强调处理者负有持续告知义务。北京四中院在“蔡文宗诉京东案”中,将“合同必需”范围限缩于基本服务功能,禁止借合同履行之名行数据过度收集之实。这种司法限缩解释,实质重构了企业与用户的议价能力平衡。
权利救济的多元路径
救济机制的效能直接影响权利实现程度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69条引入过错推定原则,将举证责任倒置,显著降低个人维权门槛。在“张奚诉网易案”中,法院虽未支持“大数据杀熟”主张,但通过审查算法透明度、概率公示等要素,确立了自动化决策的司法审查标准。这种审查方式既避免了对技术黑箱的过度干预,又维系了用户对算法决策的质疑空间。
公益诉讼制度的激活拓展了保护维度。检察机关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,已从最初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,扩展至APP违规收集、人脸识别滥用等新型场景。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,2023年此类案件赔偿金额中位数达80万元,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显著提高了企业违法成本。

技术治理与多方协同
匿名化处理成为平衡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的技术杠杆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73条将匿名化定义为“不可识别+不可复原”的双重标准,但司法实践面临技术动态性的挑战。上海法院在某医疗数据共享案中,认定经差分隐私技术处理的病历数据仍具可识别性,判决确立了“技术迭代背景下匿名化认定需个案评估”的裁判规则。这种动态认定方式,既避免技术滥用导致隐私泄露,又为科研数据合理使用保留空间。
多方共治体系的构建尤为关键。主导的负面清单制度、企业的分类分层管理、个人的数据素养提升形成治理闭环。如《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意见》提出的风险预防机制,要求对生物识别等敏感数据设置采集红线,这种分级管理策略在深圳数据交易所试点中,已实现数据交易量提升30%的同时违规率下降15%。平台通过可信执行环境、联邦学习等技术手段,正在探索数据“可用不可见”的新型保护模式。
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框架逐渐成型。GDPR的“充分性认定”机制与我国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三章形成制度呼应,上海自贸区推行的“数据海关”试点,通过安全评估、标准合同、认证等多路径协同,为企业跨境数据传输提供合规指引。这种制度创新既回应了数字全球化需求,又筑牢了国家安全屏障。
插件下载说明
未提供下载提取码的插件,都是站长辛苦开发,需收取费用!想免费获取辛苦开发插件的请绕道!
织梦二次开发QQ群
本站客服QQ号:3149518909(点击左边QQ号交流),群号(383578617)  如果您有任何织梦问题,请把问题发到群里,阁主将为您写解决教程!
如果您有任何织梦问题,请把问题发到群里,阁主将为您写解决教程!
转载请注明: 织梦模板 » 数据隐私法律中的个人权利如何保障